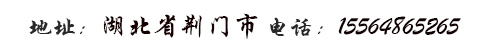阿雷维伯克与边沁的功利原则
|
阿雷维(-,法国哲学家、史学家) 作者:阿雷维 译者:曹海军张继亮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ID:baoshouzhuyi) 本文共计字数,阅读约需要17-21分钟。 按:本文节选自阿雷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曹海军、张继亮译,商务印书馆,年,第-页。原标题为“与人权宣言相对立的功利原则:伯克与边沁”。《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是英国功利主义研究的名著。在功利主义盛行的19世纪,伯克常被称为“历史功利主义者”或“保守功利主义者”,虽然这一标签如今已不太常用。本文有助于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思考伯克,集中阐释了伯克的偏见(prejudice)理论和惯例(prescription)理论,后者也可称为因袭理论。 在9年9月4日——“年革命”纪念日,不顺从国教的教堂一直保持着在该纪念日举行纪念仪式的传统。在这天,普莱斯医生在旧犹太人基督教聚会厅发表了一个布道演讲,其主题是关于“爱我们的祖国”,或许它还被称为“论爱国主义之真伪”。真正的爱国主义既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宪法优于邻国的法律与宪法,也不意味着憎恨他国。它只意味着“我们对人类中一些人的爱多于对其他人的爱,这与他们与我们的亲密程度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权力对他们有用的程度成正比”,它也要求我们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在真理、德性与自由方面一天比一天更兴盛。年革命是第一场自由的革命,它使三种基本权利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在宗教信仰方面拥有的自由权利。反对滥用权力的权利。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因其行为不当罢黜他们以及为我们自己构建政府的权利。”英国国王是欧洲仅有的合法国王,是仅有的其权威来自于其臣民同意的国王。但英国的政体仍然没有实行绝对的宗教信仰宽容原则而且也没有确立所有人都平等地拥有选举权的政治制度。普莱斯认为,只是在美国和法国,他才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而且,他用一段得意洋洋的“西缅颂”结束了他的布道演讲。 “我亲眼看到了知识的传播,它削弱了迷信与谬误的影响——我亲眼看到了人权比以前得到更好地理解;各国渴望自由,尽管他们好像没有理解它的含义。——我亲眼看到了三千多万人充满愤慨地、坚定地摒弃了奴隶制度,用不可压制的声音要求自由;他们的国王带领他们走向成功,而专断的君主则降服于他的臣民。——在分享了光荣革命所带来的好处之后,我有幸目睹另外两次光荣的革命。——而现在,我想,我看到了自由的热情正在熊熊地燃烧和迅速传播开来;我看到了人类事务正在获得普遍的改善;我看到了法律的统治替代了国王的统治,牧师的统治的地位正让位给理性与良知。” 尽管演讲地点是如此神圣,但听众仍爆发出阵阵欢呼;第二天,他们聚在一起,决定发给法国国民代表大会一封信件,事实上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国民代表大会以一份正式文件答复了这些不顺从国教者。两国革命者之间的通信警醒了伯克,他决定以驳斥法国革命原则的方式对此做出响应。经过一年的努力,他的影响轰动的《反思法国大革命》面世了。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他持续进行七年之久的反法国革命运动的决定性的一步,这场运动也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哲学家。从历史的角度看,就像他反对普莱斯一样,他毫不费力地证明了年革命既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哲学革命,而是一场“维护稳定性的革命”(revolutionofstability),这场革命在特别时刻为了保卫受到威胁的贵族政治传统是必需的。然而,很快,他就开始讨论与革命有关的哲学问题。这种哲学,即法国大革命的“形而上学”,就是人权理论,它在一个庄严的宣言中得到阐述:人一踏入社会,就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政治社会就是为了保卫这些权利而建。在这些权利中肯定包括公民自治的权利,或者说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统治者的权利,而选出的统治者只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必须执行他们的意志否则就要被罢黜。 现在,为了反对这一理论,伯克没有试图去再用菲尔麦的古老理论,即天赋君权的“形而上学”。这已经是一个被驳倒的理论,现在只有一些“奴隶制的狂热支持者”还在信奉它:“国王,在某种意义上,毫无疑问是人民的仆人,因为他们的权力除了以普遍利益为目的外别无其他合理目的”。这样,伯克,像边沁一样,运用了功利原则。当他在年还是起义的美洲殖民者的合法拥护者或“受雇的代理人”时,他就已经持有功利主义的观点了。他不允许自己提出权利问题,而是坚持这一事实:唯一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权宜问题。在2年,他采用功利观点,他批驳了“人作为人就拥有权利”的“法律的”理论。就像他后来说的那样,政治学说应该通过其实践结果来判定:“政治问题主要并不涉及真伪。它们关乎好坏。如果其结果是坏的,那么它在政治上就是假的:如果其结果是好的,那么它在政治上就是真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想要追溯功利概念的历史演进,特别是追溯功利概念将要但还没有与民主概念联系起来的人来说,伯克的政治学说都会引起他的兴趣。 伯克更欣赏普莱斯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公民政府是人们基于防范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受到侵害的审慎而建立的制度,即:“政府是人们为满足其需要而基于其智慧的创造物”。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需要可以被称作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这些需要中的每一种需要的自由地得到满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权利。但是,如果“公民社会人”需要自由,那么,他同样需要受到限制。伯克采纳了社会契约理论,他适当地对它加以阐述并强调了其权威的面相。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激情带来有害的后果——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它们加以约束。现在,这一约束必然要预设权力的存在,这种权力是外在的,并且高于那些服从这一约束的人们之上。因而,如果约束是社会的根本性要素,那么一个人被看作进入社会的行为就是一种放弃的行为,一种放弃行使他被赋予的主动权力的行为。 休谟、亚当·斯密和边沁都批判了社会契约的概念,因为他们把这一概念与反抗权利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伯克采用这一概念是因为他在其中发现了谴责诉诸暴动这一行为的根据。社会契约意味着人是受束缚的,而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可以自由地随意否决社会关系。对任何采用普遍功利观点的人来说,人民主权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人能够充当自己的案件的裁判”。人们无从证明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其利益相符。人民主权,即大多数人的绝对权力,与君主的主权,即一个人的绝对权力一样,在法律上是专断的,所带来的结果是有害的。 从功利主义哲学出发,伯克推导出一种反民主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人权理论是一种虚假的“形而上学”,是文人和哲学家的作品,他们这些人真正应该为法国大革命负责。现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正是这些反动派作家在很多方面成为了“形而上学主义者”。与深受德国哲学影响的柯勒律治一样,他们把社会看作是不同于构成它的个体的一种实体,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然而,现在功利主义者们却变成了民主主义者。如何来解释这两种对立哲学之间立场上变化呢?人们所做解释是:即使在政治科学被看作是一种功利科学时,人们仍然可以用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作为一门证明性的演绎科学(如年的功利主义改革家们所理解的那样),或者作为一门经验性科学(如保守功利主义者伯克所理解的那样)。 伯克在他的一次议会演讲中提道:“人是根据与其利益相关的充分动机而去行动,而不是根据形而上学的玄思去行动”。边沁可能也说过与伯克相类似的话,但伯克又说道:“亚里士多德——伟大的推理大师——郑重而合宜地告诫我们,正如要当心所有诡辩中的最荒谬的言论一样,我们同样也要当心道德争论中这种虚妄的几何学式精确。”如今,这种诡辩,如果这算是诡辩的话,正是边沁哲学的基础,因为他想把几何学的或是“算术”的精确性引入道德语言之中。伯克在他的《法国革命论》中写道,“政治科学就像医学和生理学一样是一种经验科学”,而且它“像其它经验科学一样不能以先验的方式被教授”。政治哲学家必须采用的方法是观察现存社会。一个社会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对其有利的根据,这是它满足人们的需要并最终实现国家真实目的的最初的证据。一个民族或一种政府形式存在了很长时间这一事实是它充满活力的进一步证据;它经受住了了敌对力量的冲击,并且表达了一代又一代人累积起来的经验。这种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因此也必然是保守的政治哲学被归结成两个理论:偏见理论(thetheoryofprejudice)和惯例理论(thetheoryofprescription)。 在伯克看来,偏见是我们道德构成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任何希望毫无成见地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人都会被迫回到第一原则上去,并被迫在他自己所面对的需要做决定的每一个问题上重建一套完整的哲学。因此,他会责备自己是个完全无行为能力的人。正是成见、先入之见和已有观念给予一个诚实人的生活以一贯性和持续性,并使德性成为习惯。成见在道德伦理中和资本在政治经济学中起着一样的作用:它是一种道德资本,没有它,行为就没有根基。它是一种个人可以独自积累但不可能积累到足够多能起作用的资本:它需要好几代人的合作;成见是民族累积起来的经验。有德性的人热爱成见,“因为它们是成见”;真正的哲学家——与那些为了摧毁成见而批判成见的法国的伪哲学家正相反——是为了发现隐藏在成见中的深层智慧。 宗教是“我们首要的成见,它并不是缺乏理性的成见,而是包含着深刻和广博的智慧”。通常,这种成见由道德乐观主义和一种信念——宇宙以及包含其中的人类社会来源于意在促进人类幸福的良善上帝的意志——而构成。所以,社会通过宗教这一手段被证明是正当的,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伯克否认他正返回到宗教“对人民有益”这一理论上:说宗教是一种必要的成见并不是要把它与有用的错误混淆起来。就宗教非常古老,并且它建立在长久经验基础之上并且与人性中最深刻和最多的期待相一致这一点来说,它是真实的。宗教以及道德伦理——它和宗教是不可分的——是我们心中最明晰地带有永恒标记的东西。法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希望革新宗教和道德。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有革新和革命;但在道德伦理方面不存在创新一说。 贵族政治的偏见在两个方面几乎和宗教偏见一样是根本的和重要的。 首先,它把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引入到社会构成之中。人权理论家们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把社会看作是由个体构成的集合体,仅仅把它看作是由当下存在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而且他们所犯的错误还在于他们认为社会只通过(by)而且只为了(for)当前一代而存在。“个体的利益”,边沁写道,“是唯一真正的利益。要照顾好个人……人们能想像到有人会如此愚蠢以至于钟爱后代超过当下一代;以至于更钟爱当下不存在的人胜过当下存在的人;以至于以促进那些还没出生的,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出生的人的幸福为借口而折磨活着的人吗?”与边沁一样,伯克从同样的原则出发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他的推理却有所不同。当下的一代和过去的世代以及未来的世代息息相关,过去的世代的经验是宝贵的,而未来世代的利益也和现代人的利益一样值得尊敬;当下一代与过去的世代和未来的世代的这种整体关系就是社会本身。亚里士多德式的社会制度赋予社会以家庭的特征;并且,一个民族的确是一个家庭的反映。这也是英国政体的优点。“我们拥有可世袭的王位、世袭的贵族、下院以及一个继承了源自于古老祖先的特权、选举权和自由的民族”。 对伯克而言,这种政治制度似乎是深刻反思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遵循人类本性而带来的幸福结果,这一结果是无须反思或超越反思的智慧。革新精神预设一种利己主义气质和狭隘见解为先决条件。而且,一个民族可以被比作一个拥有传统规则的法团(corporation),一个可以将过去的世代的遗产传给未来世代的遗产的法团。理论家们徒劳地拒绝承认法团拥有人格,而认为它只是一种虚拟体,并宣称“人作为人只是独立的个体,此外之外别无他是”;这些理论家错了。在经济学上,伯克和亚当·斯密的观点一致,因此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联盟与法团精神的敌人。难道他认识到了他所阐释的功利原则使他得出了与经济学说完全不同的政治学说了吗?而这两种学说通常在逻辑上被认为是遵循相同的原则。“民族”,他说,“就是法团”。 伯克引入其他人的思考——不是教条主义者的思考而是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考——来为贵族政治式成见进行辩护。在一个社会中,当等级荣誉因长久传统的影响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时,这一荣誉就不会再激起较高等级之人身上的骄傲,也不会唤起低等级的嫉妒感。因为较高等级的人毫不担心地享有无人与之竞争的等级荣誉,而低等级的人甚至不会想到要嫉妒他做梦也不会去追求的地位。直到贵族政治式偏见的力量使这样的等级荣誉不可动摇,两个阶级之间形成一种联合,一种构成骑士精神的情感上的联盟。但是,唉,随着革命式的平等主义的到来,“骑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诡辩家、经济学家以及精于算计的人的时代紧接而来:欧洲的荣耀永远地灭绝了”。因此,功利主义道德观使伯克得出了与边沁截然不同的社会观点:他不再谴责情感,相反地,却颂扬情感。 过去,伯克遗憾的是封建制度存在于其中的“观念与情感的混合体制”,以及“所有令人愉悦的典故,它们使权力变得温和,使服从变得可以容忍,它们使各种各样的生活变得和谐,通过温和的同化作用,它们把使平民社会美化而柔和的情感与政治融合在一起”。教条主义者和社会学家道德观的不同之处在此可见一斑。后者总是试图保护社会情感(它们的实际存在是通过他的地方性体验展示在他面前的)——团结精神、家族精神、传统的精神:此外,当作为辉格党的喉舌的伯克在为美国人的事业辩护时,他就已经是一个贵族政治论者了。而另一方面,前者通过对地方传统的抽象,把社会看成是精密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这项科学关心的是是否有可能确立普遍有效法则:从这一点人们就可以看出边沁和法国雅各宾派之间在精神上存在共鸣,尽管边沁此时还是一个托利党分子,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此时正忙着批驳9年法国大革命的诸原则。 此外,人们有可能消除所有的不平等吗?那些完全是习俗性的而且被指斥为是迷信的偏见的不平等肯定能够被废除。但还有一些不平等是自然的,这些也是所有不平等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首先就是命运的不平等:即使在所有条件都平等的情况下,金钱仍会产生重要影响。伯克曾就那些在印度发财的“富豪”、欧洲冒险家们对雅各宾派在英国事业所持有的普遍的同情这一点评论道:“他们难以忍受的是他们发现他们现在的重要性和他们的财富不成比例”。法国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在那里,纳税的农民和文人结成联盟,他们把使人民的怒火朝向教士们的财产权和贵族的特权。毫无疑问,在年之后,伯克被迫承认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和所有的贵族统治一道瓦解了。但人们之间还存在另一种不平等,人权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力量的不平等。随着法国所有建制性权力的解体,只有一种权力保持其力量,因为它被武装起来了——即,军事权力。 边沁如果人们将成见理论转化成它的法律形式,它就变成了惯例原则。“根据惯例所获得的权利是一切权利中最稳固的,这不仅对财产而言是如此,而且对确保财产安全的政府来说也是如此。” 首先,在私法领域中,惯例是财产权的基础。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情感——期待的情感。现在每个人很自然地期望保有他所拥有的;如果他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他就会感到失望。他享有他所拥有的东西的时间越长,如果失去了它的话,他就越失望。如果他长期享有这一所有权,以至于他已记不清它最初的由来,那么,如失去它,他就会无比失望。因此,以这种纯粹保守意义上的方式来理解正义的话,它就不只是对已获得权力的尊重,而且,从财产权建立在长期拥有它而取得相应权利上这一方面来说,财产也是正当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辨认出休谟的以及也是边沁的财产权理论。然而,边沁在其财产权理论中用平等原则限定了安全原则:这一限定在伯克的纯保守主义理论中不存在。接受了财产权权利的人应该从不会问财产之前是否靠暴力还是欺骗来获得的:法律时效观点就是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dangsiduna.com/ydsdms/7735.html
- 上一篇文章: 以永不毕业见证中农创学院的大爱
- 下一篇文章: 看风景还要人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