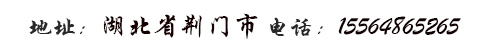康子兴丨牛顿式自然法学家亚当midd
|
北京哪家的白癜风比较好 http://m.39.net/pf/bdfyy/ ▲AdamSmith(-) 牛顿式自然法学家:亚当·斯密的启蒙 作者康子兴 文章刊于《知识分子论丛》第10辑 图片来源于网络,注释略 内容导读:亚当·斯密的哲学代表并反映了其时代的精神。启蒙之光照亮了自然界,也引入了道德世界,试图照亮政治和社会的洞穴。斯密便是此思想运动最为重要的代表。牛顿的物理学将自然界当作客观的认知对象,力求发现其中不变的运动规律。在重建自然法的努力中,斯密也预设了客观伦理秩序的存在,道德哲学遂转变成为关于道德情感的认知理论。“自然社会”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涵,自然法体现为对其客观秩序的认知,即内涵的“自然正义”之要求。经斯密改造的“自然法学”决定了其政治理论的诸多特性,是理解其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键。 好似由神那盗来了火种,牛顿的物理学既照亮了自然的洞穴,也影响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道德、法律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政治的洞穴。亚当·斯密面对着一个已被启蒙了的世界,走在启蒙运动的途中,却多少有些迟疑,不时回过头去,遥望古典之光。斯密的身上同时聚集了“启蒙”与“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的两种倾向。他对政治和宗教自由的主张、对世俗的普通生活(secularordinarylife)的维护、对商业社会的拥护是启蒙的努力;他对自由可能带来社会分化的担心、对商业繁荣可能危害个人德性、导致社会腐化的批评是反启蒙的表现。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中,斯密该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他是现代社会的批评者,还是重要的积极建设者?不管答案是前者还是后者,斯密都应该是我们思考现代政治、社会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甚至正因为其学说显现出来的“启蒙”与“反启蒙”之两面,斯密才更为重要。这双面的对勘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亦可使我们认知到:人类彻底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出于某一个思想家的煽动,亦非多人共谋的结果,而是存在着激烈的撞击、辩驳,是运动与反动之合力的产物。 ▲牛顿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霍布斯的政治科学、曼德维尔的政治经济学顺应并融入启蒙运动的大潮,推动着现代性的浪水滚滚向前。就像一个医师通过解剖的方式认识人体、生命,他们也采用解剖学的技艺来认识政治和社会共同体。在他们的手术刀面前,伦理和道德丧失了古典的高贵,转变成虚荣和自私自利的产物。在这样的伦理图景中,法律也失去了伦理根基,转变成主权者的意志。斯密怀有尊古之心,要在这喧嚣的启蒙世界中重建道德哲学,甚至力图完善前人所述颇多的“自然法学”,既还伦理德性以尊严,亦为政治和法律实践寻得“自然法理学”基础、为之提供一套“适宜”的立法者学说。斯密的“伦理——法学”理论结构颇类似亚里士多德学说体系中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系。他的学说可谓“巍巍然有古风”,然而,他所接受的世界是一个启蒙了的现代世界,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必然以之为前提,并将进行中的启蒙运动推向更深处。 本文旨在论证:基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敏锐洞察、对霍布斯等启蒙思想家的激烈批评,对古典学说,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心有戚戚焉”的深切同情,斯密提出了一套理解、建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完整方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斯密“发现”了理解和维持社会的“真理”。承接哈奇逊、休谟的努力,斯密力求通过牛顿的“自然之光”来审查伦理道德世界。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经验研究找到道德“真理”、以及认知道德“真理”的方法,斯密力求为已然动摇的“自然法”重新夯实基础,从而成为“一切政府和法律的总原则”。在斯密的解决方案中,自然法彻底失去了“神圣法”(divinelaw)基础,彻底解决了格老秀斯所遗留的问题。斯密从根上为传统自然法动了大手术,并为政治经济学和《国富论》的写作提供了可能。唯有从这一点上,我们方能理解亚当·斯密政治哲学的独特性。 01 亚当·斯密的“古今之争”: 古典与现代的合题? 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教授期间,亚当·斯密已有一个十分完备的学说体系,其内容涵盖了自然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在其后多次出版的《道德情感论》中,他也一再陈明自己宏大的著述计划:要探讨万民万世法律的总原则,以及法律和政府在万民万世中的不同演变。斯密的雄心尚不仅限于此,他还要依据它自己的原则将前人的学说重新冶为一炉,或批判、或继承、或加以修缮,最后形成的,自然是最完备的体系。在《道德情感论》的第七卷“论道德哲学诸体系”中,斯密依照他设定的范式,评点了古今产生重要影响的道德学说。此卷所凝结的是斯密对道德哲学史的陈述,然而历史述说的后面却隐含着自己的意图。阅读此卷可以得到一个总体印象:霍布斯、曼德维尔是他的主要论战对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是他心仪的哲人,并认为他们的伦理学与自己的学说完全一致。前两者是曾掀起轩然大波的现代政治、伦理的倡导者,而后两位则是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古典思想家。因此,笔者将其称为潜藏在斯密著作中的“古今之争”。 ▲道德情操论的内容(来源:搜狐网) 可以做出合理推断:斯密有意从古典学说中吸取营养,力求在后霍布斯的世界中重建伦理和政治理论。但这一扬一抑是否意味着对古典的简单借取?或者如其所说,他的学说相较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无二致?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妥善回答,除了对两者进行比较之外,还需回到斯密自己的论述中去。此乃第二重意义上的“古今之争”,亦即斯密在道德哲学史中的位置问题。 在斯密看来,道德哲学的任务不外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 1)德性之本(Natureofvirtues)。 德性由何者构成?何为德性行为、气度的要旨和品质,正是它们构成了卓越和值得夸耀的品质。依此维度,历史上诸道德哲学体系可分列入三个部类:由合宜(Propriety)构成的德性体系、由审慎(Prudence)构成的德性体系、由仁慈(Benevolence)构成的德性体系。合宜是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德性的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认为柏、亚两位古希腊哲人的学说与自己一致。在柏拉图的体系中,灵魂就像一个小共和国,由三部分的官能构成:理性的判断力(reason)、易怒的激情(Iraciblepassions)、多欲的激情(concupiscible)。这三部分合于理性的和谐便形成了审慎、勇敢、节制、正义诸种主要美德。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诸种美德乃是合于理性的中道习惯。无论柏拉图所谓的和谐也好,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goldenmean)也罢,他们所描述的都是行为之合宜。 2)嘉许的原则(principleofapprobation)。 我们通过何种心灵官能和力量对诸品质做出判断:何者正确、何者错误、何者值得称赞、何者应受谴责?同样,依此维度,史上的道德哲学体系亦可归入三个部类:分别以自爱(self-love)、理性(reason)、和情感(sentiments)为嘉许原则的体系。在第一和第二个部类的论述中,斯密均举霍布斯(Mr.Hobbes)的学说作为例证,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批评。首先,霍布斯学说的自爱基础无法解释人性中所存有的“同情”(sympathy): “同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认作自私原则。当我同情你的悲伤或者义愤,可以伪称我的情绪是以自爱为基础,因为想到你所处的情形,并思考如果我在相同的情况中将会有何感受。但是……当我因为你死去了儿子而宽慰你,要体会到你的悲伤,我并不考虑如果我有个儿子并且失去了他,我该遭受怎样的痛苦;而是考虑如果我是你,我将会怎样悲痛,我不仅与你更换了环境,我还跟你改换了人和个性。”其次,有关对错的最初感觉(firstperceptions)、作为一般原则基础的其他经验均不可能来自理性,而是即刻的感觉和情感。 需要注意的是,斯密在论述道德哲学的第二个问题时,柏(Plato)、亚(Aristotle)二人并不在他举证之例。这意味着他对霍布斯的批评并非纯粹站在这两位古典哲人的立场。细细究之,如果要将他们伦理学说的基础按照斯密的方式归类,那么只有理性一栏合适。尽管他们学说的基础迥异于霍布斯的“机械论理性”(reasonofmechanicalism),却依然是一种“目的论理性”(reasonofteleology)。而斯密恰恰否定了理性原则,而将伦理基础立于情感机制:同情(sympathy)。也就是说,在“嘉许原则”这一问题上,斯密与古典哲学相左,这便与斯密竭力标明与古典德性一致的姿态相互矛盾。 在对第一个问题的论述中,斯密的重点批判对象是曼德维尔(Mandeville),霍布斯亦未出现。这或是因为在霍布斯的体系中依然可以依稀找到德性的痕迹。“德性是对人类社会的极大支持,而邪恶则是社会的破坏者”。尽管在霍布斯看来,社会是个人的避难所;个人需要社会乃出于自私的理性考虑。而曼德维尔则否定了一切德性,为恶德张目。因此,曼氏的学说无法归入斯密设定的任何一栏中,唯有另辟一章专门批驳。 仔细考察亚当·斯密对这三者的不同态度,以管窥豹,我们可以洞见斯密对道德问题的真实态度。曼德维尔犯有彻彻底底的错误,德性和伦理秩序乃是真实存在的。以霍布斯为代表、将道德伦理建立在自私和理性之上的现代学说亦难以站得住脚,不仅基础不牢,对道德本性(natureofvirtue)的论断亦多悖谬。斯密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德性表现的描述,但抛弃了为其德性学说提供绵绵动力的“目的论”逻各斯。 因此,斯密的“古今之争”并非“是古非今”,其学说中所体现的“巍巍古风”亦仅留得古韵的形貌,而尽丧其神气。对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他对哈奇逊(Hutchson)的评述。弗朗西斯·哈奇逊(FrancisHutchson)是亚当·斯密问学格拉斯哥时的老师,亦为早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在斯密篇幅不大的学术史中,哈奇逊有着特殊的地位:唯一一位在两个问题中都加以评述的哲人。在第一个问题上,斯密批评了他的老师,认为仁慈并不能涵盖德性的全部,并肯定了合理的自爱和审慎。在第二个问题上,斯密继承了他的道德情感论,并加以发展修缮,形成了自己的“同情”机制和“无偏旁观者”(impartialspectator)机制。因此,斯密学说的精神乃是源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纯然现代的。或可以说,斯密用古希腊哲学的酒瓶,装上了启蒙运动的新酒。 甚至这“酒瓶”——其学说体系的外貌和骨架也难以“古典”冠之。我们经过以上的梳理,不难发现斯密论述的内在困难。斯密将道德哲学划分为“德性之本”与“嘉许原则”二题,从而搭建了一个探讨道德哲学的全新框架。根据斯密,这个框架当是普遍适用的,因此史上一切关于道德哲学的思考均可置入这个框架之中进行讨论,并必然分为两题。或言之,对斯密而言,此乃任何道德哲学体系之两面,缺一不可。 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刚好相反,斯密对决大多数道德体系的评述均只限于一个问题,也很难找到两者之间有何必然的联系。比如我们可以在第一个问题上与古典保持一致,而在第二个问题上则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否定。如是看来,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分立的,它们之间并不具有斯密力图建立的必然联系:一个问题上的谬误并必然产生或者归结于另一问题的错误。 ▲ThomasHobbes(-) 再来看斯密对霍布斯的批评,正因为他对“嘉许原则”的论述是错的,所以他的德性观念也有极大问题。仅仅通过自利的理性并不能确保我们对美德心生景仰,而非的通过“同情”(sympathy)不可。“当我们在这个时代称赞加图(Cato)的美德、嫌恶喀提林的罪恶(villanyofCatilline),这并不是说一方带来好处或者另一方带来痛楚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的情感。”因为年代之久远,加图的美德与喀提林叛乱不会对我们自己以及社会产生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唯有通过同情机制,设想我们身处当时的情景中会有何得失、作何感想,这种“赞赏”或是“嫌恶”才可能产生。霍布斯自利理性原则所推出的结论是:社会是战争状态下个人的避难所,是一种人为的机械,而德性(virtue)只不过是使社会机械平滑运行的诸种品质。斯密当然不会认同此德性观念,根据他的论述,其谬误乃是源自“嘉许原则”的错误。 此批判的逻辑如果加诸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自然同样适用,因为他们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情感主义”的伦理学,“同情”也无处可寻。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实际消解了古典的德性观念,借启蒙的推力将其推向现代性的深处。 由是观之,斯密的内在困难来自于其审视道德哲学史框架的固有缺陷。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诸体系并不能套用“二题分立”模式进行考量。比如,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定义为“灵魂的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德性之所以表现为某种中道乃是实现至善——幸福的必然要求,而非普遍人性中某种心灵官能的悸动。因此,亚氏的哲学并不存在斯密所述的两个问题的分立,或者说它们是合于一体,不可分裂的,这样才构成其德之本性的真貌。 这种道德哲学二题的划分不啻为斯密的一大创造,这个框架本身代表了一种思考道德哲学的全新方式。斯密将道德哲学分化成人性的道德官能及其认知对象这一内一外的两个问题:道德官能是内,指的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或同情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植于人性中类似于视觉和听觉的感知能力;认知对象是外,指一种客观的伦理秩序,亦如视听是对外界客观实在的感知。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感论》及《法学讲演录》中一再强调的,人天生为社会的动物,而社会状态即为所谓的自然状态,即便其最野蛮的形态(狩猎社会)依然不失为一种社会模式。社会本身便意味着一种伦理秩序的存在,此皆自然所为。狩猎社会向商业社会发展的历史是逐渐文明化的历史,也是自然伦理秩序逐渐实现、完美的历史。于是,道德哲学由追求幸福和“好生活”的古典学问转变成为一种认识“社会”的科学。 正因为这一转变,尽管斯密“嘉许原则”认为并不具有任何实践重要性,但却是《道德情感论》的核心问题,此即“同情”和“无偏旁观者”的心理机制。 02 同情与无偏旁观者 《道德情感论》第一章的标题为“论同情”,和《国富论》第一章的标题(“论劳动分工”)一样,它们都揭示了将要论述的主题:“同情”的心理机制乃是“道德情感”(moralsentiments)起作用的基础。在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同情”所指并非怜悯,而是一种中性的心理机制,借此可以使双方在任何情感上取得一致。以“同情”为基础便决定他的道德哲学(moralphilosophy,根据亚当·斯密,它包括了伦理学和法理学)必然是一种旁观者的学说(theoryofspectator)。于是同情又有双重意涵:一方面,既指旁观者对行为者(agent)的同情,即旁观者根据对行为者情感的认可与否做出道德判断;另一方面又指旁观者对旁观者的同情,即另一旁观者对此道德判断的认可。据此,同情的链条可以无限延展,将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同情网络。依照链条上的远近不同,同情的强弱难易程度亦有区别,从而形成某种“差序格局”,反之亦然。 同情之网必然与社会关系的网络完美重合,因为同情需要以“社会”为前提,在人人孤立,相互冷漠甚至彻底无知的状态中,“同情”不可能发生。旁观者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便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情的对象是纷芜杂的情感,正是喜怒哀乐的互动才产生了道德判断。在此意义上,以“同情心”为基础的伦理学乃是一种反理性的情感主义(emotionist)。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产生于情感,或者产生自情感的互动。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感论》第七卷所揭示的,道德情感的同情机制乃是属于“嘉许原则”问题的讨论范畴,因此它不过是一种心灵所具有的道德认知机制。正如同情先验地存在于人性之中,伦理与道德规范也先验地存在于社会秩序之中。在斯密看来,德性(virtue)是能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做出合宜(propriety)行为的品质,也就是使行为合于伦理规范的品质。人们正是在社会的互动中通过互为旁观者的“同情”方才认识到并培养起正义(justice)、仁慈(benevolence)、自制(self-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dangsiduna.com/ydsdms/7718.html
- 上一篇文章: 达尔文比亚当斯密更懂经济听牛奶可乐经济
- 下一篇文章: 以永不毕业见证中农创学院的大爱